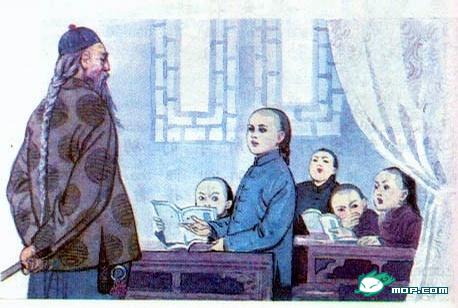当代中国书院之文化担当
2014/9/6 热度:175
书院之设为传统中国所独具之教育方式,起源于唐代,兴于北宋,完备于南宋,历元、明、清而兴衰沉浮长达千年之久,至清末变法图强而将书院改制为学堂,使书院退出历史舞台。时至当代,中国官方及民间书院再次复起,但对传统书院之文化担当意识已然淡漠,故实有重新梳理之必要。 一、中国书院之源流 有史可考之民间书院可追溯到唐朝初年,“最初只是士人读书治学之所”,后“将其服务范围从个人扩展至众人,负起向社会传播文化知识的责任,开始了传道授业的教学活动”。但此时之书院,无论在其学术理路,还是在社会影响方面,都没有达到后来书院之规模与功能。析其原因,一为初生事物发展必然历一渐进之过程,书院发展还在探索之中;二为中国文化自“轴心时期”起转入“道术为天下裂”之局面,又历秦始皇“焚书坑儒”,自汉至唐又有外来佛学进入,其间又有魏晋玄学兴起,致使中国文化之道统已失,故后来才有韩愈辟佛老,以继孔孟之道统。故其时之书院缺少正统之学术理路,无法担负起中华文化道统传承之使命。唐玄宗时期,中央政府亦设立书院,有丽正书院、集贤书院之设,但主要只是修书之所,而兼容一些文化、政治、学术活动,并非真正“传道授业”意义上之书院,但这种官办书院对书院制度之传播及民间书院之发展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 中国书院制度之兴盛开始于北宋时期,其时书院数量大增。据考证,北宋共有书院73所。当北宋初立,无力兴办官学,故鼓励民间兴办书院,强化书院之教育教学功能,使民间书院逐渐取代官学成为当时中国主要的教育方式。在此制度下,出现了书院与科举相结合,书院学生直接参加科举,获取功名;官府则把书院视为养士之所,加以扶持。此时书院,多得政府赏赐田亩,作为教学育人之资,书院规模不断壮大,其中不乏具有全国性影响力之著名书院,如白鹿洞、岳麓、应天府、石鼓、嵩阳、茅山书院等,都是其时著名书院,史上有不同版本的北宋“四大书院”之称,足见其时书院之发展壮大与影响。北宋书院之规制亦走向健全,书院有明确之学规与不同等级之授课人员,许多学者名人走进书院讲学育人。书院亦确实培育出大量人才,人才之培养又进一步促进书院之发展。 南宋时期,中国书院制度达于成熟与完备,无论从书院之数量、规制、质量、人才、学术、发展等任何方面衡量,南宋书院发展都已达于历史顶峰。相对于前代,南宋书院发展不仅数量更大,规制更完备,影响力更强,最为重要的是南宋书院出现了具有历史性影响意义之学问大家,具有独立的开创性学术理路,影响后世,实为前代书院所未有。其时程朱理学因书院而大兴,亦有陆九渊心学创世;一大批文化名人如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等理学与心学大家都于书院讲学,教化世人,并相互交流,磨砺思想,以道统传承为己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影响久远。尤其是朱熹所创之书院与讲学活动,对中国书院之发展及中国文化之走向产生了历史性影响。朱熹先后复兴白鹿洞书院与岳麓书院,推动当时书院发展,使书院讲学蔚然成风。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立朝较短之少数民族政权,但在蒙元统治的100多年间,书院却得到了官方的支持与发展。蒙元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必然要在文化上加强对中原文化的控制,为缓合民族矛盾,采取“柔化政策”,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发展和鼓励书院制度,以加强思想控制。元太宗时期设立太极书院,延请名儒赵复讲授,是为元代第一所书院。许多南宋儒者不愿在元朝做官,也退而举办书院,元政府则利用之以传播文化。元代书院因之得以长足发展,但在元政府对书院积极扶持的同时,也存在加强控制,使书院官学化的问题。程朱理学之所以成为后世官方意识形态,与元代官方对理学思想的弘扬有极大关系。 明代书院在明初近百年间处于沉寂状态,因明初几代帝王都重发展官学与科举,拉拢士人,对书院不与重视,众多学者都到官学讲学,致使书院沉寂。直到成化之后,书院才逐渐兴起,至嘉靖年间达到极盛,出现了王守仁、湛若水等历史名人所办的书院。王守仁承陆九渊心学而提出“致良知”,以“知行合一”立教,成为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心学代表人物。王守仁以其讲学推动了书院的发展,书院亦推动了其思想的传播,其身后弟子亦建书院讲学,传播其思想,时称“王学”。湛若水与王守仁同时,讲“随处体认天理”,时与王守仁切磋,亦门人众多,对书院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明代后期更有著名的东林书院,学术上反对空谈心性,重视改革时弊,关注并参与政治,对当时社会风气产生深刻影响。 清代是蒙元之后的又一少数民族政权,其建国初期,大兴文字狱,压制舆论,抑制书院发展。清初开国九十年间,只有白麓洞、岳麓、石鼓、紫阳等著名书院尚存,其他书院皆荒废。但书院制度已于中国文化中扎根,随着民间书院的自发成长,清政府开始由压制转向支持利用,由官府出资设立书院,私创书院则要经官府查核,实质是使书院官学化。在官府的推动下,清代的书院数量远超过了宋、元、明各代。但这种由官府控制的书院也缺少了前代民间书院的学术自由与思想突破,使清代书院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官办学校,并因之出现腐败现象。清朝末年,西方列强入侵,清政府被迫变法图强,改革教育制度,培育西化人才,遂将书院改制为近代学堂,使书院这一中国独具的教育制度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时至当代,书院之名又在中国大地悄然升起,各种类型的书院之名时见之于传媒。其中有官办书院,亦有民办书院;有现代书院,又有传统书院。而真正能立基于现实而承续传统,心忧天下,传圣道之学以济世者则无几。在此学绝道丧之际,实有必要重温中国传统书院之文化担当精神,进而审视当代中国书院是否有此担当,以廓清当代中国书院未来发展之方向。 二、传统中国书院之文化担当 (一)道统之担当 道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核心概念,为中国文化孳生与繁衍之元点。道统亦为中国文人所自觉传承之文化理念,而道统之传承,历来主要在民间书院之中,书院实为道统传承之文化载体。 何谓道统?就文化理念而言,此道统是以“生生之道”贯通天、地、人,是为三才之道;三才之道辅成自然万物,生生不息。故老子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易经》亦言“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为中国哲学之本体,为大道之本质,故中华文化实乃生生不息之文化。由此可解释何以中华文化能历五千年而绵延不绝,成为世界历史中唯一可以延续至今之悠久文化,这实乃中国文化之特质所决定。就学派而言,此道统以儒家为化成天下之主体,以道家为安身立命之辅翼,儒道相佐而成其用,后虽有汉唐时期的佛学进入,但中国文化以其化成之功能转印度佛学为中国佛学,终成所谓儒释道三教合流。就经典传承而言,此道统以“六经”为本,而以《易经》为宗,儒家以《易经》为“六经”之首,道家以《易经》为“三玄”之冠;《易经》与《道德经》之宗旨都讲“恒道生生”,“生生之谓易”,“生生之谓道”,只是言说方式与逻辑理路不同,儒道明分而暗合。就圣人设教而言,此道统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中经韩愈提倡,下至周敦颐、二程、朱熹兴起理学,又有陆王心学以为辅翼,以《大学》之道讲“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为“内圣外王”之学以立教。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此道统于中国文化之统治地位从未动摇,既使元清两朝为少数民族统治,亦不能改此道统,并被此道统所同化。可以想见,如果不是近现代中国士人学者自毁文化根基,进行文化自斨,任何西方列强纵能武力统治中国,亦不能灭此中华文化之道统。 此道统之传承不息,首在于中国传统书院之建制。书院本出民间,初为文人读书治学之所,后扩以为教书育人之处,虽常得官方之支持、干预,甚至控制,但书院之本从未改变。书院之设本无世俗功利之求,此由中国文化特质所决定,中国文化自古即“谋道不谋食”,“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书院文化志在思天地自然生生之理,求人类大生命生生不息之道。书院多处江湖之远,而与天地自然相亲近,淡泊名利,与世无争,但却心忧天下,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担当精神。故书院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生命之重要载体,无论朝代如何更迭,世道如何混乱,中国人之文化生命总在民间得以传承;纵外族入侵,国运衰颓,中国文化之生命力仍然生生不息,并最终为国运的再次复兴注入文化血液。 回望历史,让人不胜感慨,书院之制实乃中华文化传承之大智慧、大功德;审视当下,让人不胜唏嘘,纵有诸多书院之名,而无传统书院之实,举天下能承此中华文化传承之大业者又有几人欤? (二)学统之担当 中国传统书院之学制,不同于其时之官学,更不同于当代之义务教育。书院之设,为民间自办,以名儒大家为教授,以道统、圣人之学立教,求学者皆慕名向学而求教,皆有问道之心。问道必虚心,师道必尊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故道不轻传,必得“诚意正心”而后得之。故书院教育之原则是“有往学,无往教”,非虚心问道之人吾不教也。《易经·蒙卦》卦辞亦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此为中国传统教育之特质,虽“有教无类”,但“教有差等”,因为孔子言“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老子亦言“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故书院教育实乃开放式精英教育,即敞开大门,任何人皆可入书院问道求学,但非“士志于道”者,则吾我不教也。相对于当代之精英教育所存在之分配不公,与义务普及教育所存在之人才偏废等问题,书院教育则恰当地取其中道,让有志于道之能者得书院之资助成其大器,而让无志于道、无能于学者免占教育资源。故此书院之学统实乃古代之“素质教育”,当代教育可资之典范。 书院之学统,不只在于求学者之虚心问道,因材受教;而且在于师道尊严之标示。书院之学统,绝不只为学生所设,更是为师者所设,而且对为师者要求更严。韩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师者之职首在“传道”,即道统之传承问题。道已如上所述,为中华文化之本根,师道则为传此道统而设,师道依此道统而存,“道之不存,师之不存”,此为师道之根本宗旨,为师者必先坐拥此道,先以此道自立,而后方可以之教国人。师者之职次在“授业”,此“业”非今所谓知识也。《易经·系辞上》有言:“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师者所授之业乃是“可大”之业,非一衣一食之眷顾,故为“大业”;而“可大”求于“有功”,“有功”求于“易从”,“易从”求于“简能”,“简能”则为坤道之功。故此“大业”根源于《易》之门户——乾坤之道,根源于“一阴一阳之谓道”,故“授业”实传道于人而使人“得道”,是为“德”,“德者,得也”,得道之谓德,“以德润身”,是为“富有”,故“富有之谓大业”。师者之职再次为“解惑”,解何惑?解问道之惑,解受业之惑,非谋食之惑也。故樊迟问为农为圃之事,孔子告之以“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此衣食之谋,非师者之所虑也。故“传道、授业、解惑”实乃一事也,皆为道之事也。 当下之学校教育,皆功利之学,唯金钱事功之所图,世人皆被物化而成生产之机器,人文精神丧失,“上帝死了”,“哲学死了”,“科学死了”,“人(也)死了”。在一片“终结”声中,无人预知人类会走向何方,“盲人骑瞎马”的危险正在向人类袭来。而当代之书院,于此传统书院之学统还能有所担当吗? (三)生命之担当 按传统书院之宗旨,为学即为道,为道即为人,因为道即“生生之道”,生此天地万物与人类大生命之道,故传统书院之为学皆为求生命之学问。孔子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此“己”即为内在之生命本真,此“人”即为生命外在之附着,“为道”即求此贯通己与人与天地万物之生生不息之生命之本,故使中国文化在学术理路上成为注重内求之学,而对外在事功不甚强求。“立德、立功、立言”为中国文化所重之“三不朽”,但最重要者乃“太上有立德”,人之德行才是为人与为学之根本。故中国传统书院之设教,首重身心性命之学而轻视事功,虽亦有空谈心性之偏颇,但于整个人类文化大生命之发展方向实为有益,足见书院之道统与学统皆本之于人之生命。 纵观历代书院之设及所传之业,皆为名儒大家,得道之士,为弘道而立说,为自我生命而学术,为安顿世人生命而传道授业。人之生命,为人类认识之最大奥秘,为人类知识终极之迷。人类一切认知,皆从自我之生命存在出发,无生命存在即无此认知,生命存在为人类认知之前提;而生命发出此认知之目的,自然归于生命本身,即生命之存在,最终只能以自身为目的,而无外在之目的,故一切外求之学,最终都要回归到生命本身而求解。西方人正因为不解此生命认知之本质,一味外求而不返,只能在对象性求知中迷失生命自我,被迫把自我交给上帝,而自从尼采宣布“上帝死了”,西方人的生命就没有了根基,陷入了虚无。中国文化则以反观内照之精神,守住生命之本真,以道德之学引领学者“返本归根”,领悟自我生命之奥秘。但中国文化又不象印度文化自闭于一己之了悟,苦行自虐而绝弃一切外物;而是“从容中道”,“民胞物与”,“推己及人”,“内圣外王”而化成天下,此为人类生命文化之大智慧。故传统书院不只是圣贤设教之地,更是风化社会,化成天下,安顿世人生命之所。 观中国历史可以得之,无论朝代如何更迭,世道如何混乱,中国人之生命意识从无现代人所承受之虚无感,因中国文化是有根之文化,中国文化是安顿人身心性命之文化,而传统书院则为这一文化传承之火炬,深扎民间而风化社会,持守道统而源远流长,使中国人之身心性命得以安顿,此为传统书院不朽之功业。而当代中国书院,可有此担当意识?可有此担当之能力? 三、当代中国书院之文化担当 以传统中国书院之担当精神考量当代书院,可以辨别出当代书院多是空有传统书院之名,而无传统书院之实。以发展之眼光观之,当代具有传统书院之特质,而又有相当影响力之书院,唯有蒋庆所创之“阳明精舍”与鞠曦所创之“长白山书院”,故当下有“南蒋庆,北鞠曦”之称。但二者又有所不同,蒋庆治学专注于“政治儒学”,治《公羊春秋》而以“王道政治”立教,提出“重建王道政治,确立政治秩序三重合法性”,意在让当下社会体制接受其政治儒学思想,重新以儒教立国,从而实现传统文化之复兴,其本在政治。鞠曦治学专注于孔子《易经》与老子《道德经》,提出“儒道会通”以立教,以“正本清源,承续传统;中和贯通,重塑传统;中学西渐,开新传统”为学术宗旨和思想理念,培养“内道外儒”之“治平”人才。意在先廓清传统文化而后复兴之,以真正之孔子、老子思想化成天下,其本在生命而不在政治。此为鞠曦与蒋庆之根本不同,下面展开而论之。 (一)蒋庆“阳明精舍”之文化担当 蒋庆对道统、学统之担当皆涵摄于其“王道政治”之下。其“重建王道政治,确立政治秩序的三重合法性”包括:“大一统确立政治秩序的超越合法性(第一重合法性);施仁政确立政治秩序的民意合法性(第二重合法性);复古更化确立政治秩序的文化合法性(第三重合法性)”所谓“超越合法性”又称“神圣合法性”,实质就是道统问题,即政治秩序之建立要有“超越神圣的形上根基”,而中国文化之“形上根基”就是“道”,也就是要求国家政权之建立要符合中国文化之道统要求。所谓“文化合法性”又称“历史传统的合法性”,实质就是学统问题,以“确立源自本民族传统的历史文化的合法性。”而“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正脉是伏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的古圣人之教”,故此文化合法性就是“周孔之教”。而所谓“民意合法性”又称“法理合法性”,则是政治秩序问题,可以说与人之外在生命相关,而与人之内在生命安顿无关,但蒋庆亦有“心性儒学”以安顿己心与世人之心。 总而论之,蒋庆之“阳明精舍”具有传统书院之文化担当精神,且有自己之学术理路,并时与同道相往来,有诸多文章著作见之于世,具有一定影响力。但儒家立教终在于风化社会,化成天下,而此“王道政治”能否得以实现,则为当世诸多学者所怀疑,更妄论世人了。而蒋庆对道统、学统、生命之担当,皆系于其“王道政治”之下,如果此“王道政治”不能实现,则此道统、学统、生命之担当都无法实现,故此担当是有待之担当,不能于当下世俗之中立地生根,风化社会,必待国家政权之支持才可能最终立地生根而化成天下。这大概也是其从未开山门广收弟子,以从事传统书院教学活动之原因吧!而在当下社会政治经济稳定发展时期,其学难以看出为当世所必须,故其影响只能限于政治儒学之提倡者,欲真得以实行,当为时尚远。故蒋庆之“政治儒学”当《乾》卦九五“飞龙在天”,虽为化成天下,然不当其位甚或“亢龙有悔”是也。 (二)鞠曦“长白山书院”之文化担当 与蒋庆“政治儒学”之“飞龙在天”不同,鞠曦以“君子儒学”立论而强调“潜龙勿用”(《乾》初九》)。鞠曦以“儒道会通”立教,以“内道外儒”安顿生命,此为千古未有之特异之论。而此论之出,又有其内在理据,乃其生命体验与哲学理路自在发展之必然。鞠曦之学术理路本于孔子《易经》,而又贯通于老子《道德经》,而之所以能打通孔子与老子,实现“儒道会通”,又源于其自我之哲学体系之构建。 中西哲学理路与思维方式之不同为学者所公认,历来为阻碍中西哲学交流之主要障碍。鞠曦通过深研中西哲学之内在理路,于上世纪80年代初创立“时空统一论”哲学体系,并在此过程中形成自我独创之哲学方法论——承诺推定法;又以“时空统一论”与“承诺推定法”解读《易经》哲学,形成“形而中论”,从而贯通中西哲学,使中西哲学以时空为基点展开对话,揭示出中西哲学存在的内在问题与可能进路。 鞠曦根据“时空统一论”揭示出许多新的哲学命题。(1)“时空”是哲学之基本问题,因为时空是最基本的哲学概念,是一切概念之起点,任何概念与观念都根源于时空。时空是人类思维的背景,人类认识的起点,人类的一切思维观念都可还原为时空问题,故时空为哲学之基本问题。(2)“自以为是”是哲学之根本问题;因为任何哲学思想都是思者于当下时空限定之中的有限表达,只能“是其所是”,而不能涵摄时空全体,故只能是有限时空中的“自以为是”,而后来之思者认识到前人的“自以为是”,就又以其当下时空中的“是其所是”批判前人的“自以为是”,但这一批判仍是一种“自以为是”。故鞠曦给出的哲学定义是“哲学是对自以为是的自觉与反思的思想理论学说”。故中西哲学史都在探讨如何走出“自以为是”,而西方哲学终因走不出“自以为是”而走向“以非为是”,“自欺欺人”,最终“哲学终结”。而孔子《易经》与老子《道德经》都走出了“自以为是”,实现了“所是其是”,“和中为是”。故鞠曦以“时空统一论”解读《易经》哲学,将《易经》哲学外化为“形而中论”,即以现代理性的思维方式,用“时空统一论”将《易经》哲学以现代话语方式表达出来,“形而中论”即《易经》哲学原理的现代话语表达。这无疑是《易经》研究之一大创举,使现代人可以现代理性走进充满奥秘的《易经》,又走出哲学史的“自以为是”。根据《易经》哲学,鞠曦又提出命题:(3)“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哲学之核心问题。 鞠曦以“儒道会通”立教之根据就在于《易经》与《道德经》对人类生命终极关怀之共同眷顾,都承诺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内在价值追求;二部经典之核心理念皆为“生生”之“恒道”,“生生之谓易”,“生生之谓道”,此为中华文化之大本大源。鞠曦根据《帛书周易》解读“易有大恒”,非恒无道,非恒无生,“生生之谓易”;以之贯通老子“道可道也,非恒道也”,“生生之谓道;“恒道生生”而“儒道会通”。 鞠曦根据《说卦传》解读出孔子如何以《易经》为载体,以作传解经之方式承诺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价值论追求,并具体解读出《说卦传》所揭示之“天地损益六卦”,天道以《恒》、《既济》、《损》三损卦行其损道,地道以《咸》、《未济》、《益》三益卦而行其益道,人道处天地之中,可行天道之损,亦可行地道之益,故人当“避损行益”,实现生命之超越。而此生命之超越正是老子《道德经》所求,老子之“恒道”只是对《易经》“生生”之道的又一种言说,本质为一。故儒道本然会通,非强求其会通。 由此可见,长白山书院立教之本只在于人之生命,其“内道外儒”乃生命本真面相,只因“道术为天下裂”而出现后世“儒道相黜”之误读。故长白山书院之道统担当是“正本清源”之道统,具有对治当下社会病痛之思想资源,亦为当下现代性生存境遇所必须,故具当下风化社会之功能。故长白山书院开传统书院之学统,每年夏季举行研修会讲,“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乾文言》),全国各地学子不惧遥远,共登山门而求学问道,为当代书院向传统书院之复归树立了一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