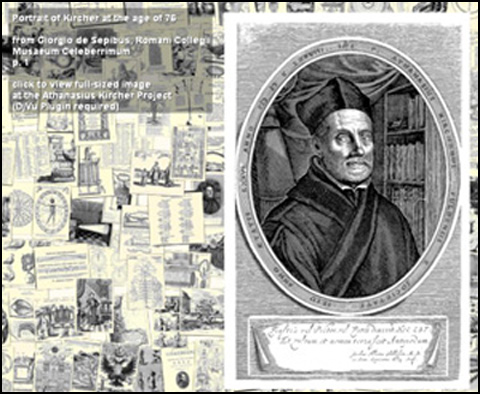基歇尔笔下的中国
2014/9/6 热度:407
对17世纪的欧洲人来说,遥远的东方是一个神奇的梦,从15世纪开始到入华耶稣会士,一本本游记、一封封书信,像一阵阵清风吹进欧洲那中世纪的城堡。异国的风情,悠久的文化,富饶的物质生活,美丽的传说,所有这些都令欧洲人砰然心动。于是了解中国、遥望东方成为社会的时尚。在这期间德国耶稣会学者基歇尔的《中国图说》,是推动欧洲“中国热”的最重要、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是欧洲十七世纪著名的学者、耶稣会士。他兴趣广泛,知识广博,仅用拉丁文出的著作就有40多部。有人说他是“自然科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机械学家、哲学家、建筑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东方学家、音乐学家、作曲家、诗人”(G.J.Rasen Kranz),“有时被称为最后的一个文艺复兴人物”。(《简明不列颠大百科全书》) 他是来华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的数学老师,与许多到东方传教的传教士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卜弥格(Michel Borm,1612-1659)、白乃心(Jeam Grueber,1623-1680)等。白乃心从欧洲来中国以前,曾和基歇尔商定,他将随时将在东方旅途的情况告诉他。卫匡国、卜弥格因“礼仪之争”返回欧洲时都曾和他见过面,提供给他许多有关中国和亚洲的第一手的材料。 基歇尔正是在掌握了这些传教士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凭借着自己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想像,写了《中国图说》。这部书共分6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碑,共有6章;第二部分介绍的是传教士在中国各地的旅行,共10章,从马可·波罗到白乃心、吴尔铎的西藏之行,将中国、中亚、南亚的许多风俗人情、宗教信仰作了详细介绍;第三部分介绍了中国及亚洲各地的宗教信仰,共7章,在这里他向欧洲的读者介绍了中国的儒、释、道三种教派;第四部分是介绍传教士们在中国各地所见到的各种人文与自然的奇异的事物,共有11章;第五部分向人们展示中国的庙宇、桥梁、城墙等建筑物,只有1章;第六部分介绍中国的文字,共5章,基歇尔首次向西方人展示了中国文字的各种类型。拉丁文版《中国图说》1667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中文全名为《中国宗教、世俗和各种自然、技术奇观及其有价值的实物材料汇编》,简称《中国图说》,即“China Illustrata” 《中国图说》的拉丁文版出版后在欧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第二年就出荷兰文版,1670年出版了法文版,它的内容被许多书籍广泛采用,这本书不仅被当时的欧洲学者所看重(如莱布尼茨案头就有这本书,并对他的东方观产生影响),同时它又为一般读者所喜爱,因为书中的插图很美,以致欧洲许多藏有《中国图说》的图书馆中的这本书的插图全部被读者撕去。这一点法国学者艾田浦的话很有代表性:“尽管编纂者是一个从未去过亚洲的神父,但此书的影响比金尼阁的《游记》影响还要大。”《中国图说》1986年英文版译者查尔斯·范图尔(Charles D.Van Tuyl)说在“该书出版后的二百多年内,在形成西方人对中国及其邻国的认识上,基歇尔的《中国图说》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最重要的著作”。 考察西方早期汉学史,基歇尔的这本书是必须研究的,它是西方早期汉学展史的链条上一个重要的环节。由于篇幅有限,下面仅对《中国图说》中有关大秦景教碑和有关西藏的报导作一评述,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中国图说》对大秦景教碑的介绍 来华耶稣会士中最早向西方报道《大秦景教碑》的是来自意大利的罗雅谷(Jacques Rho,1593-1638),尔后还有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阳玛诺(Emmanuel Diaz Junior,1574-1659)等人,来自葡萄牙的曾德昭(Alvare de Semedo,1585-1658)在他的《大中国志》一书中就曾较早地向欧洲报导过《大秦景教碑》,虽然他们对《大秦景教碑》的介绍早于基歇尔的《中国图说》,但从对欧洲的影响来说,《中国图说》对《大秦景教碑》的介绍远远大于《大中国志》等书。根据耿的介绍,从17世纪到20世纪三百年来外国学者对西安大秦景教碑的研究有40多部著作,从出版的时间上来看基歇尔的《中国图说》排在第11位,但在以后的时间里,受到基歇尔译文影响的研究者,无论是批评他、赞成他还是重复他的有9人之多。他们分别是安德烈·米勒(Andre Muller);雷诺多(Eusebe Renaudot,1648-1720);叙利亚的约瑟夫·西蒙·阿斯马尼(Joseph simon Assemani,1687-1768);方济各会夏尔·德·卡斯托拉诺神父(Charles de Castorano);第一个俄译本的学者斯帕斯基(G.Spasskii);十九世纪在中国颇有影响的裨治文,世界一流学者伟烈亚力(Whlie)景教;法国学者鲍狄埃(Pauthier,1801-1873);法国传教士达伯理。(参阅耿《外国学者对于西安府大秦景教碑的研究》,见《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一期。)这些足以证明基歇尔《中国图说》中对西安大秦景教碑文解释的影响。 尽管基歇尔对大秦景教碑的研究错误很多,但他仍其不可抹杀的学术地位,这表现在以下三点: 首先,他根据第一手材料,报导了该碑文的发现过程。对于西安府大秦景教碑发现的报导在《中国图说》出版以前有1625年罗雅谷的拉丁文译稿,但此译文并未公开发表,只是手稿。1629年有邓玉函(Jean Terrenz,1576-1630)对碑文中的叙利亚文作了翻译,但这只是部分内容。1631年的法译本,“仅译四分之一”。1631年基歇尔在他的《有关古代宗教碑文的诠释》(Prodromus coptus)一书中首次全文翻译出版了大秦景教碑,这是个意大利本,它是根据葡文本译过来的。基歇尔根据曾德昭的报导以及他1631年的意大利文译本和新的材料,尤其是卜弥格所提供的材料将其综合后译成的拉丁文本,在《中国图说》中发表。另外几个译本如1652年金尼阁的拉丁译本,1652年何大华(Antoine de Gouvea,1592-1677)的译本,影响都不及基歇尔的《中国图说》。在《中国图说》中,由于他使用了当时最新的一手材料,从而加深了西欧学术界、宗教界对这一碑文发现过程的了解。在《中国图说》中基歇尔把曾德昭《大中国志》中关于大秦景教碑的报导做了详细的摘录,并说曾德昭把“一个完全的拓印本送给了我”。这说明曾德昭到罗马时已将拓本带给了他。他还说卫匡国回到罗马时也曾当面“向我解释碑文”,他在书中也详细摘录了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的部分内容。同时基歇尔还在书中全文载登了卜弥格关于大秦景教碑的通信。卜弥格明确地说,他是该碑文的“目睹者”,他手中有关于“碑文的最准确的复印件”在此以前没有任何人像基歇尔这样对此事报导的如此充分,事实如此充足。《中国图说》中关于大秦景教碑文的译文所以来在欧洲有较大的影响,与基歇尔在《中国图说》的详细介绍有着直接关系。 其次,他首次刊出了卜弥格对碑文的注音和翻译。基歇尔对碑文的介绍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对碑文逐字进行拉丁字母注音;第二部分对碑文做逐字的解释;第三部分是对碑文做系统整体的翻译。前两部是卜弥格做的,但基歇尔首次在《中国图说》中刊出卜弥格的这个注音译文对中西双方有着重要的意义。对西方来说他们通过这个注音可以了解中文的发音,从而加深他们对中文的认识。自耶稣会入华以来他们寄回欧洲的大量的书信中不断地有对中国语、文字的介绍,其中也初步介绍了中文的发音的特点,但像卜弥格这样系统地、大规模地对中文进行拉丁文注音这是首次。罗明坚和利玛窦早已做了这项工作,如罗明坚的《葡华词典》,但并未公开发表。而金尼阁和王征的《西儒耳目资》并未在欧洲出版。在欧洲最早发表汉语拉丁注音的就是卜弥格的这篇注音。对于中国来说,卜弥格的这个注音对照表是汉语走向拉丁字母拼音化的重要文献,而长期来我们研究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音韵学的贡献,所依据的主要材料是利玛窦在《程氏墨苑》和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中的注音,材料十分有限。 最后,他确定了碑文的具体时间。大秦景教碑上关于立碑的时间有两个:中文的碑文时间说石碑是“大唐建中工二年岁在作噩太簇月七日大耀森文日建立”,即公元782年2月4日。大秦景教碑上的叙利亚文的碑文是:“Bisnat all ve tissun ve taaten diunlio,即希腊历1092年”。为什么是两个时间呢?基歇尔经过考证证明“你可从亚历山大历的1072年(这在叙利亚文的碑文中见到)减去310年(这是基督教历与亚历山大的差数)剩下的是782年,这个基督教纪年是在碑文的中文中,这同叙利亚——希腊或亚历山大的纪年是完全相合”。(有一点应注意“唐建中二年”实应是公元781年,基歇尔所有对中国的纪年都少算一年,这样成了公元782年。) 在十七世纪首次向西方报导了西藏的情况 西方对西藏的关注由来已久,柏朗嘉宾在他向教廷写的《蒙古史》中已涉及到“波黎吐蕃”(bunutabeth)的藏族情况,鲁布鲁克(William de Rubruk)也曾提到了西藏盛产黄金。意大利的传教士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1265-1331)是较早深入西藏的西方人,方豪先生认为鄂多立克“奉命回欧洲号召其他教士东来,并为探寻新路,乃由陕西、四川而入中亚,经波斯、亚美尼亚,回抵意大利……四川以后的一段路程,据游记的考证家,多认为和氏(即鄂多立克——作者注)曾取道西藏,目为第一个到西藏的欧洲人……” 16世纪以后到达西藏并向西方作报导的是耶稣会的传教士安东尼奥·德·安夺德神父(Antonio de Andrade)。安夺德神父主要在西藏的阿里西南部的扎布让,这是当时古格王国的首都,但是第一个到达拉萨,并探索一条从北京经西藏通往欧洲路线的是奥地利来华传教士白乃心,他被称为“最早赴拉萨的欧洲人”。《中国图说》是首次报导白乃心西藏之行的图书,这是《中国图说》在欧洲受到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 1623年荷兰人袭击澳门并封镇了果阿,到1661年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已完全封镇了中国港口,耶稣会来华的海上路线完全被切断了。罗马教廷和耶稣会决心寻求一条新的从中国到达欧洲的路线。此时在北京的汤若望已得知,顺治十年(1652)西藏的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来京,并受到顺治的接见和清王朝的正式册封,这样汤若望认为若取道西藏返回欧洲,肯定会得到清廷和西藏当局的保护。于是他挑选了在北京天象台工作的白乃心和吴尔铎(Albert Dorrille,1622-1662)希望他们取道西藏返回欧洲,开辟一条欧洲与中国之间的新路线,打破荷兰人的封锁。 由于白乃心离开欧洲以前曾答应将在东方旅行的材料寄给基歇尔,这样他在出版《中国图说》时就运用了白乃心寄来的材料。首先,基歇尔公布了白乃心、吴尔铎从北京到拉萨再到南亚孟加拉的旅行路线。这条路线是北京-西宁-卡尔梅沙漠-拉萨-兰古尔山峰-尼泊尔的库蒂-尼泊尔的那斯蒂(Nesti)-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尼泊尔的巴丹(Badden)-马兰加王国(Maranga)-莫卧儿的第一个城市:穆特加利-孟加拉国的巴塔那-恒河边的拿勒斯-阿格拉(Agra)。其次,他介绍了西藏的政治宗教情况和西藏的政治体制,说西藏是政教合一的王国。他还谈到喇嘛的转世和继承问题。最后,他将白乃心有关西藏的绘图编入《中国图说》之中。白乃心擅长绘画,在北京—西藏—欧洲的整个旅途中他绘了不少图画,其中关于西藏的也有几幅。这是西方人第一次通过图画看到西藏的宗教、社会和建筑的情况,因此当白乃心的这些图在《中国图说》上发表时,在欧洲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基歇尔将白乃心关于西藏的报导和绘画收入《中国图说》中,尽管有很多常识性的错误(如说西藏有两个国王),但毕竟在17世纪第一次向西方人介绍了西藏,将西方人对中国的版图视野扩展到了西藏,并“引起了对西藏的强烈兴趣”。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图说》关于西藏的介绍在西方早期汉学史中有着独特的地位。 基歇尔的《中国图说》以它精美的插图、广博的知识赢得了当时欧洲的一片赞扬,被称为“当时之中国百科全书”。《中国图说》在西方早期汉学中的地位在于它使西方汉学,使来华耶稣会士有关中国的报导走出了知识界,走出了宗教领域,而面向大众传播,如艾田浦所据说的“基歇尔神父的作品却没有直接产生任何一部重要著作。更确切地说,它的影响后来表现在了雕刻画及人们对中国问题的兴趣上。不久以后,中国问题很快成了一种时尚”。 就思想而言,基歇尔对中国的认识还是很肤浅的,他仍是在基督教历史观的构架中来理解中国,对中国文化的解释基本上是“索隐派”的方法,但对于异于基督教的东方文化他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宽容和理解,表现出了对新事的追求和探索这种文艺复兴以来的新精神。由于他本身的学者气质,他所介绍的中国给欧洲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而丰富的中国画面,在知识领域上他的介绍在许多方面也要超过前人。当然他书中的错误是很多的,这些错误同样产生了影响,在中西初识之时,这些错误是很自然的。 基歇尔的这部书是即将到来的18世纪“中国热”的前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