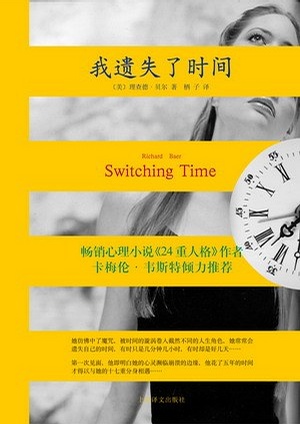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 读《我遗失了时间》
2014/9/6 热度:206
精神科医生理查德·贝尔第一次见到自己的患者卡伦·奥希弗尔是在1989年1月11日,37岁的他并没有对她留下太深的印象———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个看上去有些迟钝的女子,将与自己共同奋斗整整18年,并且在猜疑、抗拒和坚强的过程中,把住在她体内的17个不同的“人”一一融合。 《我遗失了时间》,[美]理查德·贝尔 著 栖子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 多重人格障碍,这种频繁出现于小说和电影中的病患,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是非常稀少的。对于任何一名精神科医生来说,收治这样一位患者,都称得上是难得的研究机遇,理查德·贝尔医生当然同样如此。所以当他刚刚确认卡伦的病情时,在心中洋溢起的,居然是兴奋,而非同情。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他对卡伦一步步深入的了解,他将一次次感到震惊。 《我遗失了时间》是在卡伦痊愈之后,贝尔医生留下的一部医疗记录。受过写作训练的贝尔医生把这部记录写得跌宕不已。但真正在我们心中激起震撼的,不是情节的百转千回,而是卡伦所经历过的种种难以想象的创痛,还有人体在无法想象的痛苦中令人惊异的应变能力。 卡伦找贝尔医生就诊的最初动机,是因为自己常常无端陷入沮丧当中,甚至屡屡想要自杀。更有甚者,她经常发现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要做什么———生命中大段大段的时间和记忆不翼而飞,使得她甚至无法记起自己丈夫和孩子的名字。 时间当然不会真正遗失,让卡伦困惑的,其实是居住在她大脑内的不同人格。这些“人”里,有把事情做得井井有条的凯瑟琳,她帮卡伦处理日常工作;有享受幸福人生的卡伦2,她展示卡伦身上最女性的美好侧面;有显示强烈暴力倾向的迈尔斯和卡尔,他们承受卡伦所有的痛苦记忆,在逆境中挺身而出,却也往往会突然攻击他人……17个不同的人格,各自有自己不同的记忆,他们共同的使命,就是让从婴儿时期就陷入可怕梦魇生活的卡伦,能够活下去,哪怕是分裂地活下去。 治疗慢慢深入,贝尔医生也逐渐让卡伦想起了很多早已被屏蔽掉的往事———婴儿时期就差点被父母遗弃,童年时期被父亲和祖父强暴,被强制参加邪教仪式并作为祭品被切割身体,被强迫卖YIN、偷窃……卡伦永远生活在恐惧和顺从当中。而每当痛苦无法承受之际,她就分裂出一个新的人格来承受这无法忍受的生命。当然,生活中那少数美好的部分,比如真正女性化的美好生活、对宗教的虔诚、对童年游戏的向往,也都有自己各自的分身,并且在安全的时刻现身活动———17个分身,各自有自己的名字、年龄、身份、朋友、生活,难怪卡伦会觉得自己的生命支离破碎。 面对卡伦这样一个病例,贝尔医生除了诱导之外,很少有任何过分举动。18年间,他在赢得卡伦彻底信任的同时,却失去了自己的家庭。最终,在卡伦身上安排所有生活细节的父性人格霍尔顿的指引下,贝尔医生主动出击,帮助卡伦把自己身上的17个人格一一融合为一体———这是整本书的华彩部分。作为读者,我们可以体验到见证一个新生命诞生的庄严感。当最后的时刻到来,新的卡伦诞生,她不再恐惧,也能坦然面对自己那可怕的记忆时,我们实在忍不住要为这对搭档喝彩。 故事讲完了,每个人都能从这个真实的故事中体会到不同的感受。贝尔医生说,他写下这部记录,是为了提供一个完整的医学案例。而卡伦呢,她希望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孩子们祈祷,希望自己身上的噩梦再也不要重演。至于我这个小小的读者,我为卡伦的童年叹息,也为她重生的勇气而惊叹,我对贝尔医生精湛的技艺表示叹服,但最令我震惊的,还是卡伦承受痛苦并最终修复自己的能力。 补充阅读: 本书是描述多种人格现象的作品,堪称《24重人格》的姐妹篇。但是两本书描述的角度完全不同,《24重人格》一书中,作者本人即是病患,他以自传体的形式描述了自己患病的原因,内心的挣扎以及治疗的过程等;而《我遗失了时间》一书是全球第一本由心理治疗师撰写的描绘多重人格现象的作品,将贝尔医生与患者卡伦多年来携手与难解的精神疾病搏斗,为生存的希望奋战的点点滴滴一一呈现。书中还特别收录了卡伦转换角色时的其他人格寄给贝尔医生的信件和手绘图。《24重人格》作者卡梅伦·韦斯特认为“它是一本如此重要的书,它拥有一种对人的内心洞察入微的力量,尤其是对多重人格患者的心灵世界。” 该书由美国蓝登书屋在2008年10月出版后,在纽约等地迅速成为畅销书,版权输送至英国、日本、瑞典、荷兰等十几个国家。 作为首屈一指的心理学大国,美国在这个时代仍源源不断产出着关于人性的、也许不怎么深刻却总能给人以启发的探索结果。这些渗透在学术文章、著作、通俗读物和电影中的观点,在视觉上远不如美国人抛向各个星球的一堆堆探测器械来得拉风惹眼,其长远影响却未必比不上某次还处于想象中的“星球大战”。总之,这个科学大国对人内心世界的探索力度,是值得那些对心灵感兴趣的人保持适当关注的。 《我遗失了时间》是这方面一本能让各种爱好不同的读者都能有所收获的读物。该书是美国心理医生理查德·贝尔治疗一位多重人格障碍患者的诊疗记录精编。那些渴望成为心理咨询师的年轻人能从中获得不少有用的面谈技巧,虽然当他们发现该案例的治疗时间总共持续了18年之久时可能会感到沮丧;那些想知道多重人格究竟是怎样一种状况的读者可以跟随贝尔医生的诊疗过程结识患者的17种人格,从此对“双重人格”、“三重人格”之类的小恙不屑一顾。 在一个个人主义的时代,想必大多数人都有一套关于“自我”的理论,即对“我是什么”的回答。无论“我”是“我”银行账户上的数字、“我”的所有财产、“我”的身体、“我”和周围所有人的关系、“我”的经历、“我” 的记忆、“我”的观念、“我”的感觉、“我”所占据的时间或是别的什么,这些理论都已被人一一解构。岌岌可危的“我”的性格和“我”的意识,也在这一多重人格案例中呈现了其生物性功能。 贝尔医生的这位患者———29岁的已婚女士卡伦,常常莫名其妙进入恍惚,醒来时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做着并不在计划中的事。她的生命似乎不能连贯衔接,早年的经历更是大段空白。在贝尔医生的帮助下(他坦言自己也为有幸遇到这一奇特病例而感到兴奋), 卡伦逐渐呈现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其中的各种独立人格竟达17个之多! 随着卡伦童年经历的渐渐浮现,谜底终于揭开:卡伦的每一个人格,都是为了解决某类问题而生。普通人一个人格便可应付生活,卡伦却被迫承担许多难以调和的角色:学校里的乖乖女,母亲眼中的幸福儿童,邪教聚会上的受虐狂、承担家务照顾弟弟的长女……为了让卡伦的肉体顺利完成各种角色之间的转换,并承受巨大痛苦,十七个人格一一诞生,他们以难以置信的组织和协作方式轮流出现在卡伦身上,各自负责自己擅长的工作。直到卡伦生第二个小孩时,系统运作终于出现问题,并导致了卡伦的求助。 贝尔医生弄清情况后, 借助催眠术,对卡伦展开了漫长的人格融合治疗。那些仿佛真住在卡伦心中的居民,一个个“融入”卡伦并释放自己的记忆。一次次融入仿佛一次次死亡告别,却又是一次次新卡伦的痛苦分娩。贝尔医生办公室椅子上那个备受摧残的躯体内的17个灵魂,向读者展示了心灵抗拒痛苦、艰难求生的强大力量。 正如卡伦某个人格所持观点:神赐给他们分裂的能力,以应付那些神无法阻止的事情。多重人格也不再像某些电影里有意无意渲染的那样,是一种浪漫刺激的生活方式。说卡伦和我们一样,并不是因为人人都渴望幸福美好的人生以及人人都不免遭遇种种不幸之类,而是因为我们共有一种神奇的机能,它能在最艰难的条件中保全生命。如果非要把心灵比作身体,那么多重人格“障碍”恐怕不是“残肢”,而更像是一道疤痕。它是因伤害而生,却帮助避免伤口直接暴露在空气中。那些分裂和融合的人格,那些现代人很当一回事儿、生怕遗失、迷失、丧失、丢失了的“自我”(或“自我们”),不过是生命的众多奇迹之一。 来源:南方日报 (作者:罗豫) 书摘: 护士一直叫我“卡伦”,所以我想那应该是我的名字吧。我知道我人在医院,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进来的。肚子上缠着绷带,呼吸时胸口会痛;我躺在床上——感觉自己置身陌生世界中,寂静、恐惧、孤单。我好怕自己疯了。 我被移到另一个房间。我猜我大概刚生完小孩(腹部贴着绷带,还有这一层楼全都是妈妈和新生儿)。护士走进来,掀开绷带瞧瞧;我的腹部有道6英寸长的疤,紧贴耻骨上缘,略带弧度的缝线看起来像一抹狰狞的笑容。 一名男士走进来。瘦高个儿,小平头,身上有啤酒味,脸上挂着傻傻的微笑;他对我说: 我们有一个女娃儿了。我也对他微笑。他一定是孩子的父亲,我想,但我压根儿记不起他是谁。 “卡伦,我们有了漂亮的莎拉,”他说,“你想什么时候回家?” 我不知道“家”在哪儿,也不知道家里还有什么人。 “你得先问医生,”我说,虚弱地笑了笑,“她叫莎拉吗?” “莎拉,那还用说!”他说,“难道你改变主意了?” “噢,没有啦,莎拉很美,”我说。我好害怕,脑袋糊里糊涂的,但我觉得我应该隐藏我的困惑。我怎么能问他:“你是谁?”他们一定会说我疯了。我希望我没疯。不过我很确定,一旦他们发现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一定会把我关起来。 莎拉出生后的头几天,我得知家里还有个两岁的儿子,詹姆斯,他有一头波浪般的金发和一对我见过最蓝的眸子。我在我妈带来的照片上看见他的模样。我想那人应该是我妈。她谈起生我有多辛苦:“你是第一个。第一胎最难生。我好像痛了一辈子。咱们那时跟现在不一样,哪有这么多了不得的止痛药啊!我还记得你差点把我撕成两半,害我被缝好多针。”其实她几乎不让我有机会说话,我只要听就行了。没多久,这个穿着俗气(身上一堆动物图案)、总是把话题往自己带的女人搞得我越来越不耐烦。她的丈夫、我的父亲——马丁——是个阴沉、令人畏惧的魁梧男人。他短暂现身,问我好不好却无意等我回答,看了几分钟电视节目,然后就走了。 奇怪的是,我既不惊慌、也不意外就接受了有关我和我家人的“新近才了解的现实”。虽然这一切令我十分困惑,但我隐约意识到自己过去也有过相同的处境。假装着,应付着,默默搜集各种我记不起来的信息——这感觉很熟悉,而且不知为何,我知道我最好紧紧闭上嘴巴,什么都别说。 有时候,我会在家人来访时装睡,好偷听他们谈话,偷偷了解我丈夫、我的兄弟、他们的家人以及我们的朋友。我听见我妈叫我丈夫“乔希”,他则叫她“卡特里娜”。 乔希在搬场公司当工头,负责确认货物装载是否正确,确保准时出车。他偶尔会在午餐时间来看我,但他要工作,又要照顾儿子,抽空探访对他来说有些困难。 我还不能出院。原因是我每次深呼吸,整个右胸便有如刀刺般的疼痛。后来,内科医生说我得了“吸入性肺炎”。 我发烧的状况时好时坏,却一直没有完全恢复正常。于是他们找来外科医生,把我送进手术房,切除部分右肺,医生说那儿长了一个“脓肿”。我继续在医院待了一段时间,但不清楚住了多久。 回家后,尽管右胸仍持续疼痛,我仍努力去了解自己原本是个什么样的人。亲朋好友来电问候,上门看望刚出世的宝宝;在我有办法从别处得知自己和某人的关系前,我尽可能言不及义,随便聊些什么。我找到许多相册,频频翻阅;这些相册仿佛是某人特地留给我的。我仔细阅读,发现照片底下写着密密麻麻的批注。于是我渐渐成为相片里的那个人了。 我丈夫越来越恶劣。他对我大吼大叫,因为我在医院待了六个礼拜,回到家也不能处理家务。疼痛加上疲倦使我能做的事非常有限,为此他狠狠诅咒我。我不想跟乔希做爱,我根本不认识他,所以只好频频抱怨胸侧疼痛。最惨的是,我儿子(起初他在我眼里根本是个陌生人)知道我不是他妈,于是我花了好几个月才得到他的信任,被他接纳。 但日子总要继续下去。我逐渐习惯做家务,也习惯来自乔希和妈妈的要求、命令,重新融入当志愿者、帮朋友跑腿、照顾小孩的忙碌生活。然而,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年多,我彻底陷入绝望深渊。肺部手术留下的疤痕搞得我整日难受,我频频就医,医生换过一个又一个,想找出问题所在,但没人知道为什么。除了疼痛,在我内心深处,我知道自己一直活在谎言中。我已习惯我的家人,但我的时间仍出现不连贯的空白,个中原因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会忘记自己曾穿衣打扮,或者在床边发现一本书,却不记得自己是否看过。我想我一定是哪里不对劲,而且情况很严重。我怕我会发疯,怕被关起来。我该找谁说?情况已完全失控。最后,我打了医院的紧急热线,对方介绍我找罗莎·冈萨雷斯医生,一名精神科医生。我拨电话到冈萨雷斯医生的办公室,接线员说医生已经有约了;她安排我找另一位医生就诊,冈萨雷斯医生的合伙人——理查德·贝尔医生。